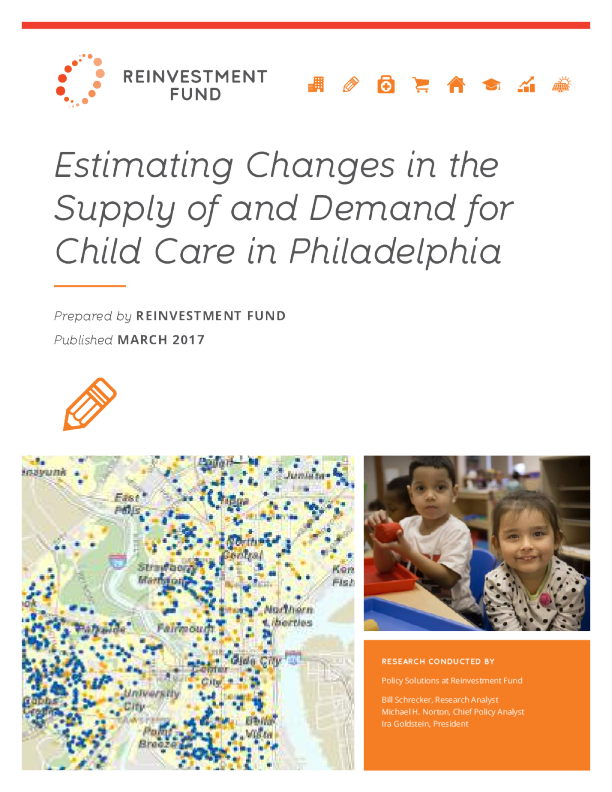Changes in the Affordability of Housing in Canadian and American Cities, 2006–2016

2020加拿大和美国城市住房负担能力的变化 ,2006–2016约瑟夫 · 菲利波维奇、史蒂文 · 格洛曼和乔尔 · 埃姆斯 2020 • 弗雷泽研究所2006 - 2016 年加拿大和美国城市住房负担能力的变化作者 : 约瑟夫 · 菲利波维奇、史蒂文 · 格洛曼和乔尔 · 埃姆斯 弗雷泽Institute. orgContents执行摘要 / i 介绍 / 1城市与经济 / 2住房成本和住房负担能力 / 4加拿大和美国大都市地区住房负担能力和人口增长的变化 / 7收入中位数和住房成本变化的影响 / 11 结论性意见 / 14附录 1 : 住房成本变量的组成部分 / 16附录 2 : 按每间卧室住房成本占收入份额排名的大都市地区总样本 (2016) / 19附录 3 : 2006 - 2016 / 30 年空间调整后住房成本占收入和人口 (% ) 的变化参考文件 / 52关于作者 / 55 致谢 / 56关于弗雷泽研究所 / 57 发布信息 / 58 支持弗雷泽研究所 / 59目的、资金和独立性 / 59 编辑咨询委员会 / 60 弗雷泽Institute. orgFilipowicz , Globerman 和 Emes • 加拿大和美国城市的住房负担能力 , 2006 - 2016 • i执行摘要通过将工人,资本,企业和思想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地理市场中,城市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加快了经济增长,提高了工人的实际收入。城市中住房的可负担性可以帮助或阻碍这种综合。随着生产力最高的大都市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工人为了在就业市场上寻求更好的机会而搬迁的意愿不仅对他们自己的命运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体经济效率和工业竞争力也至关重要。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住房的可负担性,这在地区和城市之间差异很大。特别是,如果与劳动力地理流动相关的预期生产率和工资增长部分或全部被较高的住房成本所削弱,总体生活水平可能会受到影响。本出版物提供了更好地了解大都市地区住房负担能力的演变,比较了 396 加拿大和美国大都市地区的住房成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间的变化。具体来说,我们确定了这两年中每个大都市地区每间卧室的住房成本所占总收入中位数份额的增长。根据这种衡量可负担性变化的方法,在此期间,加拿大和美国大都市地区的绝大多数样本 ( 312 ) 中,住房成本占收入中位数的比例下降。总体平均下降 7.3 % ( 按人口加权为 8.7 % ) 。然而,显示住房负担能力改善的大多数城市地区都在美国,除了加拿大的三个地区 ( 在 52 个地区中 ) 外,每个卧室的住房成本占收入的份额都有所增加。事实上,在此期间,加拿大城市的住房成本占收入的比例增加了 7.2% ( 按人口加权为 7.6% ) 。我们还探讨了可负担性变化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大多数大都市地区都能够将提高的可负担性与不断增长的人口相结合。然而,加拿大也与美国不同,52 个加拿大城市中有 46 个将人口增长与负担能力下降结合在一起 ; 这包括该国六个拥有超过一百万居民的大都市地区。然而,对于美国和加拿大样本,2006 年至 2016 年间人口百分比变化与住房收入份额百分比变化之间的统计关系较弱 ; 这表明,住房可负担性下降并不是人口增长所产生的住房需求增加的必然结果。 弗雷泽Institute. orgii • 加拿大和美国城市的住房负担能力 , 2006 - 2016 • Filipowicz , Globerman 和 Emes最后,我们将数据分解为可负担性衡量标准,以区分收入中位数和住房成本的变化,并初步了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大都市地区之间差异的原因。我们发现,加拿大城市的名义家庭收入中位数实际上比美国城市增长更快。然而,在我们的样本中,加拿大每个卧室的住房成本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美国。因此,相对于美国,加拿大住房负担能力的下降反映了加拿大城市住房成本的快速增长 — — 而不是中等收入的增长放缓 — — 与大多数美国城市相比。我们的发现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几个领域。一个是确定导致加拿大城市相对于美国城市住房成本增长更快的因素。我们的研究确定了案例研究的候选区域,以检查影响住房成本变化的因素。第二个是加拿大城市住房负担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加拿大工人的地域流动性。 Filipowicz , Globerman 和 Emes • 加拿大和美国城市的住房负担能力 , 2006 - 2016 • PAGE1弗雷泽Institute. orgIntroduction城市在区域、国家和国际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将企业,工人,物质资本和思想聚集在一起,大型集聚日益推动整体经济增长和生产力 ( 联合国,2011 ),特别是在加拿大和美国等高度城市化的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变化有助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工人需求的相关变化。因此,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是影响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弹性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住房的可负担性随着个别大都市地区就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会影响劳动力的地理流动性。特别是,由于劳动力的流入,住房的负担能力大大降低,这种现象将阻碍工人获得高薪,高质量的工作,以及企业吸引和留住员工的能力。他们需要具有竞争力。这项研究调查了加拿大和美国大都市地区在最近十年的可比数据中的住房可负担性变化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 2006 年至 2016 年。因此,该研究提供了一些间接的见解,以了解两国城市政府在如何管理当地经济增长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因为这影响了住房负担能力。它还提供了一个观点,即观察到的两国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是否可能受到劳动力流动性差异的影响,而劳动力流动性又与每个国家的住房市场行为有关。研究进行如下。I the ext sectio, we briefly discss the importat role by rba agstratios i regioal ad atioal ecoomics ad how chag - ges i hosig affordability coditios the cotribtio that idividal rba ecoomics mae to the atioal ecoomy.第三部分概述了我们如何衡量住房负担能力的变化,以及围绕衡量的一些概念问题。第四部分提供了 2006 年至 2016 年两个人口普查年度之间 52 个加拿大和 344 个美国大都市地区样本的住房负担能力衡量变化的数据。它还考虑了衡量的可负担性变化与人口增长变化的关系,以及将加拿大与美国大都市地区进行比较时,这种关系是否有所不同。第五部分确定了观察到的可负担性变化的组成部分,以便理解第 4 节中所述的观察到的可负担性变化的差异。提供了结论意见。在最后一节。 2• 2006 - 2016 年加拿大和美国城市的住房负担能力 • Filipowicz , Globerman 和 Emes弗雷泽Institute. org城市与经济关于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文献强调了城市作为创新和创业场所的重要性。1它还确定了降低住房负担能力可能对城市促进生产率增长的能力产生的不利影响 , 从而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提高家庭收入。通过允许创意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在相对较近的物理距离内工作 , 城市群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 , 早期引入和更快的采用。2 此外 , 由于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同 ( Hsieh 和 Moretti , 2019 ) , 随着生产率增长相对较慢的地区的工人转移到增长较快的城市地区 , 一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会增加。3这种劳动力重新分配的结果可能是家庭收入的更快增长 , 因为工资和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提高有关。由于在享有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率表现的地区,相对收入应该在上升,市场力量应该鼓励在其他方面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促进劳动力的地理重新分配。但是,住房成本的增加可能是限制工人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的重要因素 ( Glaeser,Pozetto 和 Tobio,2011 ) 。具体而言,住房成本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抵消工人从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地点转移到生产率增长迅速的地点所获得的名义收入的预期增长。 The elasticity of hosig spply i a locatio fially coditios how qicly shoot costs will rise as additioal worers relocatio to that locatio.4反过来 , 住房供应弹性的差异也反映了不同地点对新住房供应的监管限制的差异 ( Glaeser , Gyourko 和 Saks , 2006 年 ) 。1.例如 , 参见恩格尔、伯贝目标 - 米拉本特和皮克 , 2018 年。2.这种现象有助于在文献中描述为 “集聚经济 ” 。有关集聚经济的讨论 , 请参见 Krugman , 1991 ; Ellison , Glaeser 和 Kerr , 2010 ; 以及 Meusburger , Funke 和 Wunder , 2009 。3.全要素生产率被定义为实际产出除以用于产生该产出的所有投入的加权平均值 , 其中权重是每个投入的总支出份额。作为一个经验问题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本上反映了技术变革。4.住房供应的弹性可以被认为是住房单位存量对一单位住房支付的平均价格增加的反应。 Glaeser , Gyourko 和 Saks ( 2006 ) 为美国城市提供了证据 , 表明住房供应弹性存在显著差异。 Filipowicz , Globerman 和 Emes • 加拿大和美国城市的住房负担能力 , 2006 - 2016 • PAGE3弗雷泽Institute. org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向内移民的住房成本大幅增加而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由此产生的劳动力 “分配不当 ” 可能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例如,Hsieh 和 Moretti ( 2019 ) 估计,在 1964 年至 2009 年期间,通过阻止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地区重新分配到高生产率地区,限制降低了住房供应弹性,使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总量降低了 36 % 。简而言之,降低住房供应弹性的政策对当地经济及其居民以及国民经济都具有深远的经济影响。 4• 2006 - 2016 年加拿大和美国城市的住房负担能力 • Filipowicz , Globerman 和 Emes弗雷泽Institute. org住房成本和住房负担能力住房供给弹性决定了住房价格对住房需求变化的反应。特别是,只要住房的供应不是完全有弹性的 — — 也就是说,在不支付更高的平均价格的情况下,供应的数量不能无限增加 — — 住房的单位成本就可以随着人口的增长或家庭形成的增加而增加。5在这方面,必须区分住房成本的变化和住房负担能力的变化。特别是,如果家庭收入中位数 ( 可能与生产率增长有关 ) 的增长速度快于住房成本,则住房负担能力将提高,至少对于特定地点的中位数家庭而言。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地方的 “典型 ” 房屋的收入份额下降,则住房负担能力会提高。因此,提高住房可负担性的公共政策目标在概念上与提高住房供应弹性的目标不同,但显然与之相关,因为通过鼓励更快的生产率增长,从而提高家庭收入的政策也可以提高可负担性。在给定位置 , 最广泛使用的住房负担能力衡量标准是住房住房 ( 无论是拥有还是出租 ) 相对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中位数成本 ( 世界经济论坛 , 2019 年 ) 。大多数研究将住房负担能力衡量为住房成本 ( 有时根据住房 “质量 ” 进行调整 ) 与所有政府税收和转移之前的收入之比。6 然而 , 也有人认为 , 住房可负担性应以相对于可支配收入的住房成本来衡量 , 后者是家庭在从总收入中扣除净税收后不得不用于住房的收入 , 以及在食品等一篮子必需品上的支出也从总收入中减去。7加拿大抵押和住房公司 ( CMHC , 2019 ) , 以及赫伯特 , 赫尔曼和麦库 ( 2018 ) 表明 , 对于